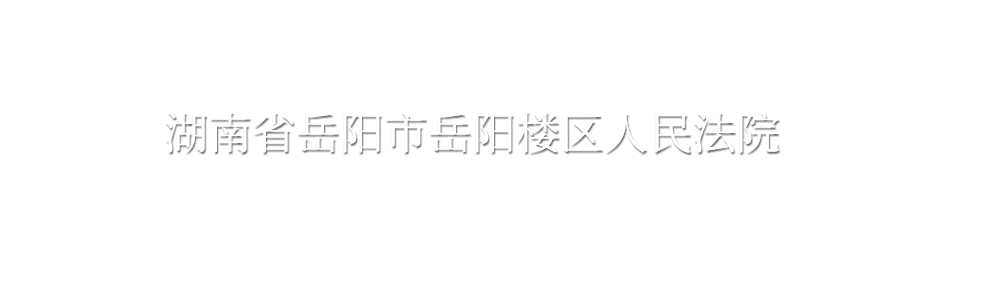□案例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案情】
原告:何丽红,女。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支公司。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原告何丽红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以下简称顺德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分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何丽红诉称:投保人黄国基(系原告之夫)生前与被告顺德支公司属下的伦教办事处营业员严小惠先后签订了两份保险合同,包括:2004年3月16日签订的人身意外伤害综合全队合同1份,保险金额为31万元,保险费为390元;2004年3月25日签订的祥和定期保险合同1份,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费为594元。上述两份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均为黄国基,受益人均为原告。2004年7月7日,黄国基意外死亡,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黄国基符合交通事故致心肺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原告认为该事故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于2004年8月27日向被告顺德支公司、佛山分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并提交了相关书面材料。二被告受理赔偿请求后,无端猜疑原告制造保险事故,拒不履行赔偿义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5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人顺德支公司、佛山分公司答辩称:被告方拒绝理赔具有充分答辩称:被告方拒绝理赔具有充分的理由。1、投保人黄国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2004年3月8日,黄国基为申请投保被告方的祥和定期保险及人身意外综合保险,提交了两份《个人保险投保单》,并在投保单中明确其当时没有参加或正在申请其他人身保险。但事实上,黄国基在此前后数日中有多次投保记录。2、黄国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具有主观上的故意。3、黄国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严重影响保险人的核保工作及对于保险费的确定,并最终导致保险人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依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审判】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投保人黄国基在投保涉案保险时是否故意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投保人是否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作如实说明,直接影响到保险人测定和评估承保风险并决定是否承保,影响到保险人对保险费率的选择。所以,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庆当如实回答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作出的询问,如实告知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设定承保条件、承保费率的重要事项。根据本案事实,可以认定投保人黄国基在投保涉案保险时,在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同类保险的问题上具有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投保人黄国基向被告佛山分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保险合同。在购买祥和定期保险时,黄国基对于投保单第三部分告知事项第十一款投保记录关于“A、目前是否有已参加或正在申请中的其他人身保险?如有,请告知承保公司、保险险种名称、保险金额、保单生效时间;B、过去两年内是否曾被保险公司解除合同或申请人身保险而被延期、拒保或附加条件承保;C、过去有无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三项询问,均填写了“否”。黄国基向佛山分公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时,对于投保单第三部分告知事项第十一款关于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既未填写“是”,也未填写“否”,即未作回答。但根据本案事实,黄国基分别向多家保险公司购买了多份了身保险,保险金额累计高达1738000元,可以认定黄国基对于保险人提出的上述问题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系出于故意。
关于被告佛山分公司、顺德支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佛山分公司解除黄国基与其签订的涉案祥和定期保险合同,拒绝对该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告何丽红要求佛山分公司依据祥和定期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投保人黄国基向佛山分公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时,对于投保单第三部分告知事项第十一款关于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既未填写“是”,也未填写“否”,即未作回答,也具有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佛山分公司明知存在上述情形,但既不向投保人作进一步的询问,也未明确要求投保人必须如实回答,而是与投保人签订了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合同,并收取了保险费,即属于主动放弃了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的权利,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弃权行为。因此,佛山分公司无权解除该合同。因该合同的被保险人黄国基已因交通事故死亡,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佛山分公司应按该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即原告何丽红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赔偿金30万元。
据此,法院判决:一、被告佛山分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向原告何丽红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金30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借款利率计算,从2004年11月22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何丽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何丽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认为:关于在投保涉案祥和定期保险时,黄国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本案上,黄国基在投保涉案祥和定期保险时,被上诉人佛山分公司就投保记录向黄国基做出了询问,但黄国基隐瞒了自己在其他保险瓮多次重复投保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与事实明显不符的答复,显然违反了如实告知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结合黄国基重复投保时间密集及其曾兼职保险代理业务的具体情况,认定黄国基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黄国基在投保涉案祥和定期保险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上诉人佛山分公司是否有权据此解除该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佛山分公司作为保险人,有权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比二款关于“关于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解除其与黄国基签订的涉案祥和定期保险合同,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纪念会保险金的责任,同时不退还保险费。上诉人何丽红作为受益人,请求佛山分公司依照该保险合同承揽保险责任于法无据,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在2002年保险法施行期间发生的案件。法院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认定即使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由于保险人对此明知而仍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据此否定保险人因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合同解除权,保险人仍应承揽该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笔者称此为保险人解除失权。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修订保险法的决定,新法第十六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六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该规定吸收了本案的裁判意旨,即将由本案所确立的保险人解除直接转化为立法条文。由此,作为“活法”载体的司法活动,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的渊源,法意经由司法裁判、立法得以凝炼——法律经验经由立法、学说得以固化这一法律发展轨迹。案例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诉讼法论的层面加强案例研究,提高案例向法律经验转化的效率,是值得我们沉思的问题。本文将围绕本案和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就保险人解除失权的问题试作一些具体的法理分析。
一、何为失权
失权,又称为权利失效,是德国民法实践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一种限制权利行使的规则,是指权利人可行使而不行使其权利,从权利人的行为中足使义务人产生其已不欲履行其义务的正当信赖,权利人之再为行使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而限制其权利之行使的规则。
(一)失权规则的法理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一般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为君临全法域之“帝王条款”。“诚信原则具有弹性,内容不确定,系有待于就特定案件予以具体化的规范,论其功能,实为实体法之窗户,实体法赖之以与外界的社会变迁,价值判断及道德观念相联系,互相声息,庶几能与时俱进”。①对于司法裁判而言,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院裁量权,是给法院的空白委任状,指引法院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证人和补充,进而解释和补充法律,以维持公平正义,使其即使造法亦不致发生偏差。②失权规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类型化、具体化,属于法院运用裁量权的领域。“权利原得自由行使,义务本应随时履行,故权利失效是一种特殊例外的救济方法,适用之际,宜特别慎重。”③
(二)失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三项:
1、情势要件:权利人可行使其权利而不行使。本项要件一般有时间限制,即权利人在相当期间内可行使其权利而不行使。唯该相当期间,为不确定期间,可由法院运用裁量权根据个案的情况定其长度。
2、信赖要件:义务人得从权利人的行为中产生其已不欲其履行义务的正当信赖。例如,买受人发现标的物瑕疵后继续使用而不提出异议;承租人修缮租赁物而多年未向出租人康王乡修缮费用等。就该要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义务人须已根据上述信赖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发,而是在当事人身上所引起的相邻权利人将不再行使其权利的信赖。”梅迪库斯(Madicus)称此为信赖投资(Vertrauensimvestition)。
3、反言要件:权利人之再国行使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权威性自相矛盾行为(2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所谓相予盾行为,是指权利人如行使某项权利,则与其以前的行为相矛盾,并将使对方对其原行为的合法期待落空。
总之,法院在对权利人之行使权利是否作失权之判断时,必须斟酌权利之性质、法律行为之种类、当事人间关系、经济社会状态及其他主观因素而决定之,应从严认定,以避免软化权利交通,使义务人履行义务道德趋于松懈。失权规则对于形成权的行使尤其重要。④
二、保险人解除失权的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的分析方法,是将某项制度加以模型化(冷背货地看亦可谓之各式化);探究某一法律事实是否适用该制度,得用该模型加以逐一嵌套,符合者得以包含,不符合者则自然突出;对于不符合者,须视其是否为例外,为例外者即仍可包含,非为例外者则宜改换模型,另觅他项缺席;如例外过多,极易构成对该项制度之反对,自非所宜。法律分析的路径,大致循此。保险人解除失权的构成要件,应当根据失权的构成要件进行细化。具体说来,有以下四项:
(一)保险人享有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事项的权利,如投保人不履行该义务将享有合同解除权。(由于2009年保险法第十六条对保险人该项解除权的构成进行了重新办公室,因而本案系适用2002年保险法,本小节将按照新法的规定进行论述。)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系采取被动告知告知主义,即投保人只须对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就其知道和应当知道的情况予以告知既可,对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则无须告知;判断投保人是否应当知道,应以一般人之常识,就投保人之地位环境、所处况判断之。依据有关保险惯例和立法例,投保人对下列事项也无须告知:(1)减少风险的任何事项;(2)保险人表示不要求告知的事项;(3)属于明示或默示保证事项。投保人此项如实告知义务,应限于在合同订立时履行,而不延续至合同订立后。投保人在合同订立后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项,即使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亦无须告知保险人。
保险合同项下的法定解除权,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分配,对投保人原则上赋予随行解除权,对保险人原则上则为禁行解除(保险法第十五条)。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据此,保险人该项解除权的构成要件,有以下三项:
1、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意和重大过失,系对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状态的限定。故意,是指投保人明知有关事项应当告知保险人而未予告知;重大过失,是指投保人对应予告知保险人的事项未尽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而未予告知。重大过失是相对于累微过失而言的,后者一般是指行为人未尽处于其地位的合理人的注意义务。上注意义务,均系客观标准,便于对行为人过失的认定。
在本案中,投保人黄国基向被告佛山分别签订了两份保险合同。首先,黄国基在购买祥和定期保险时,对于投保单中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均填写了“否”。由于黄国基的该意思表示明显与事实相反,因而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出于故意。其次,黄国基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时,对于投保单中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既未填写“是”,也未填写“否”,即未作回答。对此,法院结合黄国基生前曾从事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兼职个人寿险业务代理工作的事实,对于如实告知义务应当比一般投保人具有更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并对保险风险控制应注意的事项具有一定的了解。同时,黄国基的重复投保行为集中在2004年2月29日至3月9日之间,距涉案投保时间并不久远,不可能记忆不清。据此认定黄国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系出于故意。
2、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中心影响保险人决定是滞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第二款)。在2002年保险法第十七条中,该条影响要件只对应于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不对应于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新法将该项影响要件一律对应于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区分其究系出于故意抑或重大过失。这是符合一般人对其中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认知的。因为该项影响要件,表面上是对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限定,其实质早是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内容的限定,即投保人必须就“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而对于其他事实,即使投保人故意隐瞒,只要不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仍不享有解除权(这后一方面,正是本条修订的立法意图)。
在本案中,虽然法律并不禁止投保人在购买人身保险服务上重复投保,但法院认为,投保人黄国基所重复投保的包括涉案保险在内的各项保险,均为低保费、高赔付的险种,重复投保次数多,保险金额累计高达1738000元,相应的保险费对于黄国基5万元的年收入而言,亦属巨额。这使投保人在客观上具有巨大的潜在道德风险。在此情形下,由于黄国基系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直接影响到被告佛山分公司对其人身风险的评估,足以影响佛山分公司对是否承保、如何确定承保条件和费率等问题作出正确决策。
3、保险人该项解除权未逾行使期限。该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分有两种情形:(1)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赖帐之日起30日后消灭;(2)自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后消灭(第三款)。解除权的性质为形成权,上述期限的性质为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
(二)保险人可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而未要求。对于本项要件,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将其内容规定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在合同订立时,保险人有权要求投保人就其提出询问的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着情况如实告知(同条第一款)保险人提出访问后,投保人不就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应要求其补充告知。该款将否定在合同订立时,是合适的。所谓合同订立时,应泛指保险人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之前。保险人在合同订立后才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其解除权的行使应受同条第三款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范。在本案中,投保人黄国基在购买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时,对投保单中关于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未作回答,被告佛山分公司明知该情况,既不提出进一步的询问,也未明确要求其必须如实回答,而是与其签订了该保险合同,并收取了保险费。可见,佛山分公司在可要求黄国基如实告知的情况下而未要求。
保险人如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在事理上应不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于此情形,判断投保人是否应因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受惩罚时,亦须就保险人方面加以探究;否则只单方面就滚动条为僵化解释,一旦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直接赋予保险人以合同解除权,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同时,对于前引保除法第十六条第六款“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表述,笔者认为存在扩张解释的适用究竟。要否定保险人该项解除权,不能简单地指向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知道”,而应指向保险人对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放弃”。详言之,不管保险人对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是否知道(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不知道),只要其可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而未要求的,即符合本项要件。本案的情形,即其适例。
(三)投保人对分保险人的立约行为产生正当信赖。投保人在保险人提出询问后不如实告知,而保险人亦未要求其补充告知,使其得以蒙混过头,由此,投保人对分遣队人的立约行为产生正当信赖,即投保人得正当地认为保险人不再要求其补充告知,亦不再因此而解除合同。在本案中,被告佛山分公司在与投保人黄国基订立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合同时,在黄国基对投保单中是否向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等事项的询问未作回答的情况下,既不提出进一步的询问,也未明确要求其必须如实回答,而是与其签订了该保险合同,并收取了保险费,致使黄国基对其立约行为产生了正当信赖。对此,法院认为佛山分公司系主动放弃了要求黄国其如实告知上述事项的权利,构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弃权行为,故无权再予主张或者解除合同。
(四)保险人行使该项解除权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于此情形,保险人如行使该项解除权,将构成自相矜持行为,即其行使该项解除权的行为与其在合同订立时可要求投保人如实告知而未要求的行为相矜持,并将投保人对其立约行为的正当信赖落实,如准其解除合同,必须将有违诚实食用原则。在本案中,法院先行认定了被告佛山分公司在订立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黄国基可要求其如实告知而未要求的弃权行为,进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其该项解除权,即佛山分公司无权解除该保险合同。因该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黄国基已因交通交事故死亡,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佛山分公司应按该保险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即原告何丽红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赔偿金30万元。
(作者单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