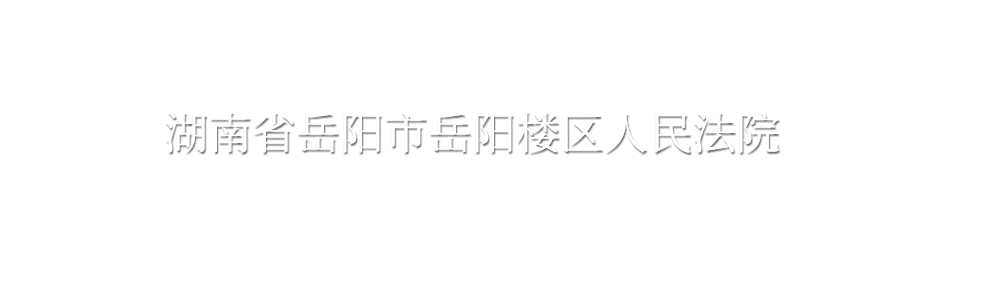光阴荏苒,岁月悠悠,日子在云淡风轻中飞逝。再过一些时日,便到父亲作古二十周年的忌日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身为人子,一直想为平凡的父亲写点什么以资纪念,因不善舞文弄墨而只得每每作罢。
父亲心地善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遇见他人有难,无不尽力襄助,并告诉我们“行善乃快乐之源”。旧时家乡附近道路下雨天泥泞不平,父亲不顾羸弱身体,总是到河滩上担沙填补,乐此不疲,使多少人免受滑倒之苦。那时正值先后建设铁山水库、中洲垸大堤、麻塘灭螺大堤等多项造福岳阳人民的善举,父亲积极参与,从不藉口躲避。在修建麻塘大堤工地上,父亲因患出血热入住医院。病愈后本可回家在村里做些牧牛之类的轻松活儿,但其主动要求再上大堤,结果因工地发生事故,致使腰部严重受损,差点客死他乡。在国家经济困难、物质贫乏时期,时有一些外地人员上门乞讨,父亲望着米缸里日益减少的稻米,毫不犹豫地盛上一小筒予以救济,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家也是举债度日,赊米吃饭,常为稻梁谋虞。
父亲一生勤苦,也时常教育我们“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在大集体时凡事抢着干,出勤不遗余力,从不怠工偷懒,屡屡赢得好评,堪称同龄楷模。分田到户后,他与母亲共同打理十余亩水稻责任田,天道酬勤,季季丰产。农闲时节人却不闲,夏天顶着炎炎烈日上街捡拾废品,或到湖滨园艺场贩卖黄皮梨贴补家用;冬季冒着“吹老少年郎”的湖风到湖洲砍割芦苇为子女换取学费。年复一年的超负荷劳累让其明显早衰,四十出头的年龄额上皱纹便刀刻斧削,顶上头发稀疏可数,腰背也日渐佝偻不直。
父亲关爱子女且快乐着我们学有所成。我们兄弟姊妹五人,那时正呈阶梯状念书,经济负担可想而知,家庭困难不言而喻。父亲不顾亲友的善意劝说,决意不让一个子女辍学在家。1985年,我被中南政法学院录取,其时大哥已在武汉纺织工学院入读二年了,三个弟妹分别在念初中、高中。父亲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脸上笑成了一朵喇叭花,其何尝不知生活的负荷更沉重了。入学那天,父亲担着木箱行李送我去江城,途中稍事休整后,我望着父亲汗湿衣背,模样苍衰,提出换挑一程,父亲笑着说:你还是学生伢,以后有机会挑担。少不更事的我未再坚持,沿着父亲洒下的汗水一路亦步亦趋,跟随前行,懵然未觉父亲的拳拳爱子之心。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其天生口吃,被人戏称结巴,为此没少受讥辱,也无疑增添了其与他人交流沟通的困难。父亲少年时体质虚弱,小病小痛缠身不断,及至中年出血热、阑尾炎等病接踵而至,痔疮也伴随其多年。1990年其患坐骨神经痛病行走不便。1991年其腹痛入院,经确诊为淋巴癌晚期。父亲得知消息后,毅然决然要求回家,不愿给经济并无余裕的家庭再添负担,并以不配合治疗相要挟。我们见其回家之意甚坚,遂遵其意愿送其回家作些保守治疗。因哥哥远在株洲工作,我便每个周末回家探视父亲,帮母亲干些力所能及之事。父亲去世前的那个周末,我因公未回家,接下来的星期三我在单位获悉父亲辞世噩耗,当即放声大哭,涕泪长流,泪飞顿作倾盆雨。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不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吗。父亲短暂的一生历经了诸多沧桑,却从不知疲倦,从没有停息,为了他所挚爱的家庭耗尽了生命中最后一滴心血,最终气竭力尽,油枯灯灭,在其五十岁那年过早地走完了其人生旅程。
奔丧回家,看到父亲双眼紧闭,整个躯体已消瘦得皮包骨头,几不成人形。我握着父亲冰凉干瘪的双手,望着父亲的遗体,想到其苦难的一生,泪水泉涌于脸眸,心里默默念着:父亲大人,您能睁开双眼吗,不孝儿有好多话想对您诉说……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被病魔折腾得苦不堪言,曾一度想安乐离世,但仍恋恋不舍地撑着,临终时还轻轻地呼唤着我们的乳名。我闻听此言,热泪再度盈眶,深悔未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个周末服侍父亲于病榻之前。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泪血染成红杜鹃”的清明节,我们来到父亲长眠的河堤一隅,望着父亲坟头的萋萋芳草,看到“纸灰飞作白蝴蝶”的情形,我跪立坟前,噙泪低语:父亲大人,如有来世,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儿子,我们再续父子情缘,您答应吗?但见微风轻拂,梅雨淅沥而下。
年届不惑之后,多少次夜深人静,我端详着父亲的遗像,想到父亲生前对我的殷殷廑注,也想起自己蹉跎的青葱岁月及现时的平庸平淡,老不上进,甚或……,深恐父亲大人九泉有知而为之下泪,一念至此,心中不乏一种沉重和羞愧之感。父亲关于为人处事的言传身教将永铭心底并时时鞭策着我们。
我爱我草根般的父亲,任时光流逝,父亲大人音容宛在,历久弥新。我对父亲的爱和思念一如那东去的大江之水,永无止息。
父爱如山,父恩难忘,结草衔环,终生怀念。
——值父亲大人诞辰七十周年、辞世二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和此方式怀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