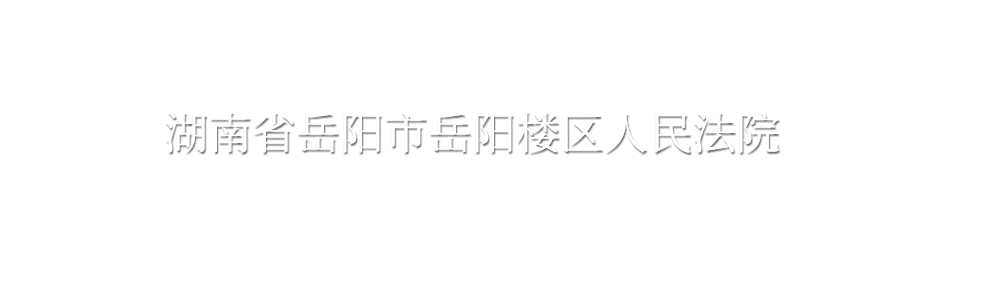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和亮点之一,也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件大事。此次改革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着手,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式和方法。量刑规范化改革对于增强人们的量刑意识,转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定罪,轻量刑”、“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观念,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打击与保护同步”、“实体与程序兼顾”的司法理念等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量刑规范化试行过程中,一些法院和法官对量刑规范化理解和认识不足,出现在案件审理时不运用或敷衍运用的现象,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次改革的质量和效果,故本人就量刑规范化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谈谈个人粗浅认识。
一、刑罚理论及刑罚适用的需要
刑法是规定犯罪行为及其法律后果及刑罚的法律规范。刑法学所研究、关注的即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基本固守在犯罪论这一理论重镇,于对刑事法条的注释,或偏重于理论思辩,普遍缺乏实证分析、对刑罚运行机制尤其是刑罚效益的实现及其程度缺乏终极意义上的关怀。在实践层面多年来形成重定性、轻量刑的固疾。沙俄时期的刑法学家基斯特雅考夫斯基曾言:在刑法中,第一把交椅无疑属于刑罚。或许基氏的言论是出于对刑罚论的偏好,但并非言过其实,至少在刑法学体系中,刑罚论与犯罪论应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实不为过。研究刑罚适用,需要改变重定性轻量刑,重打击轻改造的传统观念,刑事审判更要注重刑罚适用的效果。刑罚适用在国家刑罚权运作过程中起着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是制刑权、求刑权和行刑权有效运行的中间环节,是法官裁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罚适用模式大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刑罚制度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这些变革的影响下不断演进,从内容和适用方式上看,发展演进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普遍适用死刑、肉刑和流刑等身体刑为主,以损伤甚至消灭对方肉体、造成罪犯痛苦为目的,如奴隶制五刑、封建制五刑。第二阶段是以普遍适用监禁为主,将犯人关押在监狱中服刑成为主要的行刑方式。第三阶段是以非监禁刑为主,即从刑罚主要手段的监禁过渡到罚金、缓刑、社区劳役(社区服务)等监禁的替代措施和其他不直接控制人身而采取非监禁控制措施的中间刑罚。二十年来,我国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10%左右,超过不少年的年度GDP,这几年来,我国每年判处拘役、徒刑实刑以上的犯人占全部已决犯的63%左右。2011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2012年4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就《监狱法》实施和监狱工作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监狱681所,押犯164万人。虽然从上述数据看出我国在押犯人数没有出现有关监狱法学家十几年前所隐忧与预测的那样,暴涨至200万之多,但还是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而明显上升。同时这些数据也显示我国刑罚制度总体上尚处于刑罚适用模式的第二阶段(域外发达国家已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第三阶段)。因此,刑罚制度中的量刑已是刑事审判工作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现代刑罚平等价值理念的需求
平等适用刑罚是最大程度地保护法益、预防犯罪的要求,也是人们实现价值追求—得到尊重的欲望之要求。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还包括“比较的公正”,即通过类似案件处理结果的相互比较来体现公正。在这种意义上,公正不仅是看得见也是可以体验的公正,如基于当前监狱关押罪犯的行刑现状,相近类似的罪犯通常关押在同一监区,以便分类矫正,而判处的刑罚是罪犯在服刑期间交流最多的话题之一,此时必然存在服刑人员对类似案件刑罚的比较问题(如都是盗窃3000元,服刑人员对刑罚轻的一般会讲你法院肯定有人)。不均衡的判罚结果在这种量刑攀比的过程中常被放大,造成服刑人员“认罪不服判”的现象,严重影响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加大改造难度。因此,量刑公正被誉为“刑事正义的一半工程”,刑罚适用的平等就是要求制止量刑失衡、细化量刑规则。我国法律量刑比较宽泛,自由裁量空间比较大,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法官对案件存在不同的考量,就存在量刑就不那么平衡的现象,但这是正常的,一刀切反而不公平,因为量刑不同于证据采信、法条适用。现在人们常提到“同案不同判”现象,那什么是“同案”呢?有一句话讲“天下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比如考生甲、乙高考都考了600分,也都报考了同一所大学,但乙未被录取,为什么?因为虽然乙的其他学科考得分数很高,但数学只考了50分。这就像评价一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由该行为的情节A 情节B 情节C 情节…组成一样。同案应是综合的同案而非片面的同案,同案首先要同等被害同等报应,其次要同等加害同等处罚,最后要相对人平等即法的中立。虽然没有完全一样的案件,但刑罚处罚的差异不能太大,同一个国家、同一部刑法,作出的裁量应该是相当的,所以最高院才作出量刑规范的规定。
三、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也是人民法院“二五”、“三五”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在经过前期局部试点、全国部分法院试点两个阶段后,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并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此次改革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着手,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式和方法,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法”引入量刑活动,要求按照“三步骤法”进行量刑,而且明确规定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允许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并要求说明量刑理由,从而实现量刑活动的公开、公正。2013年1月修改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法庭调查结束后“开始就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等,将量刑程序作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加以规定。最高院原准备将量刑规范化在试行后的一至两年内在全国正式实施,现已近三年了,为何还未实施?是因为涉及对量刑规范化的认识和执行问题:在认识上没有完全统一。目前从全国一些法院量刑规范化的情况,尚有一少部分法院没有开展量刑规范化活动,特别是中院和高院开展量刑规范化活动的比例更低;还有很多法官在思想上认为量刑规范太机械、太繁琐,没有多大意义。以前量刑是采取估量、估堆的方式,现在引入“公式化”,最高院认为这样的转换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刑法规定了四百多个罪名,最高院只选择了其中的十几个试行规范化量刑,象贪污贿赂等常见的犯罪没有加以规范,这些也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认识并不断的总结经验,等条件成熟了再正式实施,所以虽然中央政法委几次催促最高院要求在全国正式实施,但最高院认为还要花时间积累经验。再是刑法修正后,还有一些罪名及司法解释还在进一步完善,那么涉及到的量刑情节也要规范和调整。如最近废除劳教制度后,一些界于犯罪与违法的行为怎么对待?不能不管,那么就要对一些罪名降低门槛。像多次盗窃、扒窃、入户盗窃入刑,盗窃罪是数额犯,现在改成了数额犯与情节犯相结合,具备法定的情节就构成犯罪,还如醉驾入刑等。目前最高院在研究起草诈骗、寻衅滋事、抢夺、敲诈勒索等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出台后将对量刑产生影响。所以量刑规范目前尚未在全国正式实施,但正式实施是不可逆转的,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