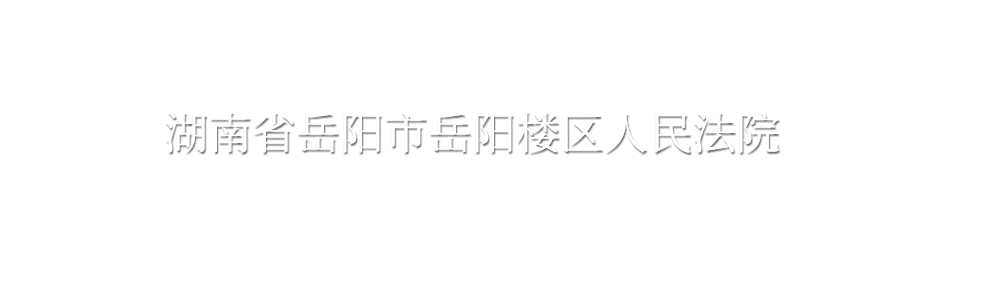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和诉讼案件复杂难解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调解作为一种比较成功的民事案件处理方式,广泛应用于民事审判工作中。调撤率还曾作为民事审判工作是否有绩效的标准,纳入法官业绩考核,成为一项衡量法官办案能力的硬指标。法院和法官或为完成调撤率指标,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斡旋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和稀泥”,或以时间为软性手段强制调解,使得一些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清楚的案件得不到及时裁判。强使当事人服从调解实现调撤结案的做法不仅缺乏法理依据也违背调解自愿的法律原则,当事人看似接受调解但却对法律和法院失去了信心。诚然,有着“东方经验”美称的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价值,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认,但法院和法官对调解制度的理解和运用,必须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审限制度,保障公平正义及时地得到实现。本文就法官职业与调解冲突机制解决进行探讨,希望能适当缓解法官当前巨大的积案压力和调解压力,从而更加职业化。
一、在审判实践中,民事调解和民事判决都是人民法院结案方式,两者在传统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分。首先,调解是基于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达成的协议,而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基于民事审判权做出的专业判断。其次,民事判决必须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做出,对实体争议没有涉及的事项法院不得裁判,而民事调解不受此限制。再次,法律不允许对调解提出上诉,而一审法院作出的尚未生效的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有权提起上诉,要求上级法院撤销或变更裁判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基于以上区别,民事调解和民事判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案方式。而大多数法官尤其是年轻法官都从内心上认同一个案子的调解要比判决难处理的多,不在于法律关系的复杂难易程度,而在于结束一个诉讼过程,是用民事判决的方式还是用民事调解的方式,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选择权掌握在当事人而非法官手中。有多少案件可以采取调解方式结案,并不由法院或者法官决定,法院和法官无法预知更无法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调解结果。
二、司法审判是一门艺术,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法官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必须具备专门的知识和专业的思维方式,因而法官职业化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依法治国和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而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更多的是协商与谈判下的利益平衡,虽然同为矛盾化解机制但与司法审判有着本质的区别。职业化的法官运用法律思维获得的裁判结果,可能与大众思维、社会情理相悖,但却是符合法定程序的依法裁判。目前,调解在民事案件的处理中,主要还是应用于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情感案件,或者以情感为基础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往往因为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需要大量法律外的引导疏通,并非仅仅是专业的法律判断。运用职业化的法官来主持参与调解,做大量法律外的工作,其结果往往过于重视社会效果、忽略法律效果,重视调解、轻视判决,重视大众化、偏离专业化。社会转型期的法官因而也被赋予太多的社会角色而不堪重负,他们既是负责专业法律判断的审判员、息诉止争的引导员、普法知识的宣讲员,又必须是生活经验丰富的调解员、不良情绪的疏导员,既要潜心审判实务的探索研究又要不断提升自身生活技能,与专业化、职业化背道而驰。
三、立案登记制以来,诉讼外调解的优势被弱化,而法官在诉讼中的调解因与审判程序交织在一起,“调审合一”、“调审不分”模式产生种种弊端,对法院和法官权威造成严重影响,调解制度难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一是立案制度调整和司法理念发生变化。立案登记制强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畅通了诉讼渠道,降低了诉讼门槛,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更加顺畅快捷,客观上导致法官在诉讼中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的难度加大。二是诉讼外纠纷化解传统优势的弱化。低成本、效果好是诉讼外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传统优势,也是当事人选择该纠纷解决途径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诉讼外纠纷化解的上述优势不明显,且在逐渐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还不完善,导致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积极性不高、对调解公信力降低,使得本来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反倒成了第一道防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三是诉讼中的调解和判决规定在同一模式中必然造成程序的不和谐和紧张,导致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
四、诉前调解前置程序的构建无疑是“审调分离”的优选衔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诉前过滤分流,不仅有助于做大做强调解,而且有助于解决法官的双重身份,缓解审判压力。诉前调解前置程序,就是在法院设立专门的调解室或调解窗口,吸纳资深退休法官、优秀人民调解员、经过专门调解培训的律师和法学专家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特定社会经验的人员组成特邀调解员,在民事案件进入法院后由立案庭对当事人推荐调解或由当事人申请调解,使调解成为必然的前置程序。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法院进行形式审查并予以司法确认,产生强制执行力。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案件自动转入诉讼程序由法官进行专业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欲达成合意的,则通过诉讼和解来解决。实务界对诉前调解前置程序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曾提出建立审调适度分工的诉讼调解新机制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为诉前调解前置程序提高解决纠纷效率,形成法官职业化认同,缓解法官职业压力,塑造法官职业尊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社会主流意识对诉讼的推崇和调解的轻视,对法官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模糊不清的今天,建立诉前调解前置程序不失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